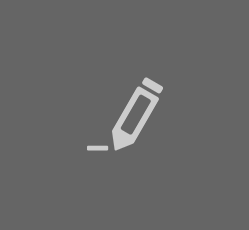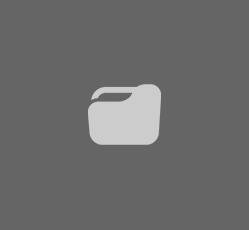-
诗心常在 翰墨风流 ——胡成彪先生的诗书画略说 马 龙
- 信息来源:寤移斋诗墨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4-10-12
- 西汉毛亨在其为《诗经》所作的《序》里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句话概括地道出了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发展进化过程。“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可谓诗之先声。胡成彪先生首先是一位诗人,这是因为与书画相比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所描写的事物最广泛,所抒发的情感最丰富和深沉。近代著名词人、学者、教育家顾随先生曾说:“凡艺术作品中皆有作者之生命与精神,否则不能成功。古人创作时将生命精神注入,盖作品即作者之表现。”其实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作者感情与精神的参与方可成功,而这作品中也清晰地反映着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情状和变化,胡成彪先生也不例外。
胡先生生长在沛县,自幼即受大汉雄风的浸染,“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诗句,在他心底埋下了开张豪阔的种子。而微山湖这一山水绝佳,四季风景殊异的宝地,以及那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信念的歌声,又滋养着他对自然,对历史、对文化具有敏锐感知的诗心。所以在胡成彪先生的诗作里,既有咏古思远的豪壮情怀,又有吟诵民间风物的清新、活泼与自然。而无论哪一点,都体现着作者的用语之真和用情之切。
观其豪,如咏《水浒英雄》一首:大路拔刀对不平,江湖啸聚是英雄。
尾联一句,英雄气概扑面而至,真令人有路见不平,欲拔刀相助而后快之感。
生时能与风雷动,去后亦留山水青。
独恨贪官锄恶吏,敢轻权贵骂朝廷。
当年若使能为伍,应占罡星第几名?
其清新明丽,如《夕照微山湖》:细浪粼粼映夕阳,云堤缈缈接村庄。
又《七绝》两首:
轻舟结队行还止,野鹜成群落又翔。
景至残时更觉好,风如湖心始知凉。
滩前日暮欲何往,渔火相连是水乡。一道短坡一片房,绵延小路过山梁。
不久前笔者有幸畅游微山湖,也曾荡舟湖面,趁夕阳而返程。今诵胡先生诗,似又觉荷风拂面,桨声悦耳,当日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村人日晌无所事,檐下相偎晒太阳。
峰头老树透斜阳,屯靠山峦路绕梁。
飞鸟怯寒归宿早,村民无事起炊忙。
其写心思性情,如《微湖晚舟》:清波映月千重影,远渡连天万点星。
身外无求心事少,泛船独享一湖风。《采桑子•过年》
匆忙未觉春晖满,岁岁新年,今又新年,何不偷此半日闲。
回头漫点去年事,骄亦无端,馁亦无端,责任依然在眼前。《向博友拜年》
清代徐增《而庵诗话》中说道:“诗到极则,不过是书写自己胸襟。若晋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 以直写其心,直抒其性的诗词创作来讲,需要作者真能直面生活之种种。如顾随先生所说:“大自然是美丽的,愁苦悲哀是痛苦的。二者是冲突的,又是调和的。能将二者调和的是诗人。”而当诗心圆融时,那么触目皆可入句,所见尽能成诗了。寻找并写出一个真我,那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停博整顿四旬半,百事无功进退难。
几欲述说别后事,奈何琐务总无端。
常怀道友斋中趣,每念诗朋网上缘。
旧日难留来日远,且迎新瑞贺新年。
诗词之余,胡先生耽心翰墨已有数年。他也曾在一篇自序中说:“书法早推古人,再效今贤,景仰苏、米高风,初得权希军、姜敦文先生之笔意。”这说明他对书法艺术还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他不单从历代法帖中寻找书法的真谛,更得到当代贤者教诲,这些都是他的书法艺术取得现在的成就的重要因素。
胡成彪先生的书法以行草书为主,作品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古人所言说的“温柔敦厚”。那是一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审美享受。书法一艺,看似简单。善书者把笔临纸,点画飞动,纵横间有君临天下之感。而此中真意,往往不能与外人道,非知者不能解也。欣赏胡成彪先生的书法,就能使人体验到那种毛笔行走在纸面上,提按转折、缓急迟涩的韵律与节奏。当今学者有论书法为纸上之舞蹈、无声之音乐,这真是说到了书法艺术的最美妙处。
书法以笔为本,以墨为用。而无论是字中的力、势、意,还是线条、结体、章法,哪一方面都需要通过笔的书写及最后的墨迹来显现。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篇》说:“盖笔者墨之帅也,墨者笔之充也;且笔非墨无以和,墨非笔无以附。”这正道出了书法艺术中笔与墨之间相辅相成而又辩证统一的关系。笔墨二者不单能反映书写者的功力水平,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境界。从胡成彪先生的作品中,观者就能感受得到胡先生的修养与性情。他的用笔气息内敛,锋芒不露,每一笔提按每一笔使转都交代得清楚明了,一丝不苟,中锋用笔更见出他为人的严谨与认真;他的用墨不湿不涩,滋润中如含春雨,不浊不滞,浓重外更显风神。
胡先生的行草多作正局,给人一种堂堂正正的威严气质,这应该与他身处要职,为一县父母有关。而细品胡先生作品,堂正之外又生出亲切和蔼的感觉,他的书写总是那样自然而然。他没有刻意地去表现所谓的书写技法,只是在临纸的一刻以情运笔,以意使墨,点画到处,随机生发,因此他的作品平实、淡宕,不激不砺,似无波澜而波澜自在其中;他没有如当今一些所谓书家那样横涂竖抹,故作高深,用才使气,以惊世骇俗状示人,他的作品总如同邻家先生,儒雅大方,博学多闻,而又真诚坦荡,平易近人。这应该是诗歌艺术对先生的熏陶与润化。
艺术的学习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任何人也走不完,任何人在任何阶段也都有存在的问题和再造新境的可能。就此点看胡成彪先生的作品,似乎有实多而虚少,今多而古少的感觉。书法之虚实简言之即作品之布白。早在《道德经》中老子就曾说过:“知其白,守其黑。”清蒋和《书法正宗》指出:“布白有三: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间之布白。” 书法的虚实问题也与黄宾虹先生曾参悟一生的:“绘画实处易,虚处难”同一道理。今古问题,或可说为取法问题。中国的传统艺术重一“格”字,即“品格”、“格调”。而一艺之成,取法很关键。古人讲“取法乎上,得法仅乎其中;取法乎中,得法仅乎其下。”其中所谓“乎上”之法,即历代高格调之作品。现代的学艺者,必先向后走,向传统看齐,入得其内,还要出得其外,几进几出才能终有所成。手下无古,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今则又徒成他人傀儡,失却我之意义。以上两点,虽数语可以道破,但真正有所证悟则需一生追求,当与不当,愿与胡先生商榷并共勉。
.jpg)
胡成彪先生不光书法写得好,他还画得一手极有情趣的好画。就笔者所见的一组雏鸡花卉来讲,虽然画面的形象相对简单些,但这画面中却藏着丰富的思想与情感。也正是这些形象之外的内容,成为胡先生的国画作品最吸引人的关键所在。
中国画最讲写意精神,无论造型、笔墨、构图,也包括题款、钤印甚至还有空白等等,都是画面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组合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胡先生的画,造型简练、生动,寥寥数笔便刻画出一个憨态可掬,活泼传神的小鸡形象。其它的物象也是数笔概括,言简意赅。有的作品甚至简练到只有一只鸡,然后是题款,印章,真是简之不能再简,少之不能再少。但为什么观者却不以为画面空洞、单调呢?道理很简单,画家虽然只画了有限的形象,却把更丰富的意蕴通过留白、题款、印章留给了观画者自己去解读。例如《乖乖鸡》其中之一,画面就只有一只雏鸡,居右而稍往下的位置。小鸡昂首向左上方,那正是题款开始的地方。题款竖写成一行,正与画幅左边线同长,这样就使画面左边密不透风,.jpg) 一来保证了作品气息不散,二来与画面右边线形成疏密对比。题款下方一方名章压住阵脚,同时又与右边线上方的两枚闲章遥相呼应。两方闲章看似微小,却在画面中至关重要。其一是跟名章的呼应,其二处于右边线的上方又与雏鸡一起起到了稳定画面重心的作用。观者试想,如果两方闲章一上一下,那么画面右边门户大开,气息尽散;如果有第三方闲章盖在画面右下方,又与左边的名章冲突,使画面板滞而气息不畅。这真是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大有四两拨千斤的风采啊。
一来保证了作品气息不散,二来与画面右边线形成疏密对比。题款下方一方名章压住阵脚,同时又与右边线上方的两枚闲章遥相呼应。两方闲章看似微小,却在画面中至关重要。其一是跟名章的呼应,其二处于右边线的上方又与雏鸡一起起到了稳定画面重心的作用。观者试想,如果两方闲章一上一下,那么画面右边门户大开,气息尽散;如果有第三方闲章盖在画面右下方,又与左边的名章冲突,使画面板滞而气息不畅。这真是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大有四两拨千斤的风采啊。
细细欣赏画家这一组雏鸡作品,耐人寻味处大多类此,但作者却不是单单只以这一招示人,而是不断变化生发,虽画面各异,而其画理却始终如一。
此外更需点出的不是胡先生作品的画面构成,而是他充满童趣与天机的作品题款。例如上面所介绍的那件作品题款曰:“不要问我哪里去,不要问我哪里来,我的名字叫乖乖。”其它如一只雏鸡仰头望右上方树枝上一只小鸟,题曰:“我不能上树,是因为我祖先太懒,这是达尔文说的。”画小鸡与一枚红果,题曰:“邻居家的果子掉到我家院子来了哦。”画小鸡俯视一只螳螂,题曰:“好像练过螳螂拳,我要小心点。”真是字字简洁却又风趣诙谐,情味绵长。这些题款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这是何等心性,何等情趣,真可与白石翁“他日相呼”、“小鱼都来”、“可惜无声”等题款共读了。
笔者不仅想起了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曾序其弟袁中道诗集说:“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脱尽近代文人习气故也。”此一段文字,被后人视为“公安派”所倡导的“性灵说”之宣言。袁宏道所论的是诗文,笔者以为,非止诗文需要“性灵”其他诸艺皆然。一个人的性情、思想、情感随其作品而得以彰显,而作品也表现着作者的才情、禀赋、修养。西人布封所说:“风格即人”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明代著名哲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无论是袁宏道所说的“性灵”,还是布封的“风格即人”,或者是李贽的“童心说”他们所看重的就是每个人尤其是艺术创作中人最真实自然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这种情感包括自身的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等。这些情感是自我所独有的,而对于胡成彪先生来说这也正是他不与人同,作品具有独特魅力,“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标志和特征。
胡成彪先生在其《走近美丽》一文中说:“诗词是人类语言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思想最生动的表现,是人类抒发情感的最佳形式之一。诗词表现的不仅是事物本身,更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诗词创作的过程,也是作者感受和走近美丽的过程。”诗歌是如此,书画也同此理。全面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本就不易,何况是像胡成彪先生这样既用心政事,又留心翰墨,既体察民心,又善养诗心,有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的人,就更显得困难了,这就如同我们无法道尽世间的美好一样。胡先生自己也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赞颂心中的美丽。或用歌声,或用舞蹈,或用诗签,或用画笔。谁能够写完世界,谁能够道尽美丽?(原载于《大众收藏》2009年10月14日、《书画艺术》2013年第1期)
作者系当代知名画家、著名美术评论家。 - 【关闭本页】 【返回顶部】 【打印此页】 【收藏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