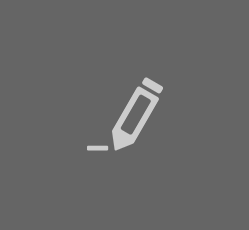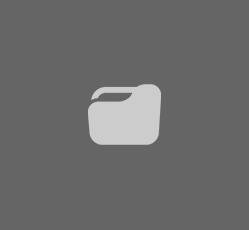-
小船无舵 舵在心中 —— 读胡成彪《沧桑随笔》杂感 康明超
- 信息来源:寤移斋诗墨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4-10-12
- 任何样式的文学艺术,都是人的情思的宣泄。
.jpg) 成彪的宣泄选择了诗词、书法这两种中国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他让周边的文人雅士们大大地吃惊了一回:谁能料到,一个曾经鞍前马后从随于领导的“丫鬟头”后又成了有“丫鬟”随从于鞍前马后的“领导”,竟有这般的情致,竟然吟得神似陶渊明的雅诗。有这种惊讶,不应该去责怪成彪。因为成彪原本就将自己撕裂了,拿出一半甩给了“官场”,留下一半存放在自己心里。时侯一到,心里那股滚烫的“岩浆”自然会喷涌而出,且宣泄得如此酣畅淋漓,让那些本以为“官”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是那个样子的人们顿然之间目瞪口呆。这更不应该责怪成彪,因为时下的“官”,大多是先做“丫鬟”,而后升了“官”有了自己的“丫鬟”,再为更大的官去做“丫鬟”。那人心里也藏了自己的一半,但决不去想什么“诗”、“书”,而是日思夜盼着别的什么。这样的“官”大家见多了,便对成彪有些不解,以为不太合时宜,未免有些迂腐。成彪取笔名“湖西迂人”,兴许,自觉世人业已这般看待,也就自甘“迂腐”了!但我断言,这绝非成彪的“自任”,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抑或大智慧的“自虐”。否则,诗里哪会有春水般的宁静、恬淡,书法又怎能如此的洒脱、奔放?
成彪的宣泄选择了诗词、书法这两种中国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他让周边的文人雅士们大大地吃惊了一回:谁能料到,一个曾经鞍前马后从随于领导的“丫鬟头”后又成了有“丫鬟”随从于鞍前马后的“领导”,竟有这般的情致,竟然吟得神似陶渊明的雅诗。有这种惊讶,不应该去责怪成彪。因为成彪原本就将自己撕裂了,拿出一半甩给了“官场”,留下一半存放在自己心里。时侯一到,心里那股滚烫的“岩浆”自然会喷涌而出,且宣泄得如此酣畅淋漓,让那些本以为“官”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是那个样子的人们顿然之间目瞪口呆。这更不应该责怪成彪,因为时下的“官”,大多是先做“丫鬟”,而后升了“官”有了自己的“丫鬟”,再为更大的官去做“丫鬟”。那人心里也藏了自己的一半,但决不去想什么“诗”、“书”,而是日思夜盼着别的什么。这样的“官”大家见多了,便对成彪有些不解,以为不太合时宜,未免有些迂腐。成彪取笔名“湖西迂人”,兴许,自觉世人业已这般看待,也就自甘“迂腐”了!但我断言,这绝非成彪的“自任”,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抑或大智慧的“自虐”。否则,诗里哪会有春水般的宁静、恬淡,书法又怎能如此的洒脱、奔放?
中国历史上有个好传统,以文会友、以诗结社,其间少了许多等阶的森严,多了些许平易的亲善。胡弦先生在《记胡成彪诗集》一文中提及:“目前人们对‘官家’作诗,常常有某种先入为主的特别心理。但这种情况,好像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古代则无有。”他列举了王昌龄、王维、孟浩然之间的“诗情”。其实,《红楼梦》也有类似的情节,在海棠诗社里,大家也都淡化了平日尊卑长幼间的芥蒂。社会、家庭皆如此,何以哉?诗赋丹青性情使然!好此者所操持的应该是一种公平的人性观照,只要不去作茧自缚,谁都可以拥有一个精神上毫无羁绊的自由空间,仅此,才会有真性情之作。舍之,便假了!不真了,哪里还有善?哪里还有美?生涩扭捏、谄媚阿谀、装腔作势……诸如此类言不由衷的所谓“作品”,总归让人心里疙疙瘩瘩堵得慌。强扭的瓜不甜,硬摘的果铁酸,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同理可证。
我向来对“诗”抱有一种敬畏之心。我认为诗歌是宣泄人类情感最为简练、最能勾魂的文学样式。我读诗,但从来不敢写诗,也便不会写诗。至于书法,更是国之精粹。毕加索曾言:假如能早一点接触到中国的书法,他绝不去学绘画!他认为,中国的书法体现了线条和色块艺术的最高境界。成彪将这两种高境界的艺术形式都揽到怀里,时时把玩,很是一种福分,真让人艳羡不已。但这并非是人即可为之的,要有天分、有才气,如田秉锷先生所说:成彪“骨相有诗”。
我和成彪的老家同属一个行政村,庄与庄相连,亲与亲相荫。在一起时,酒喝得多了点,也都是放浪形骸的一个“狂”字。分别之后,听说他当了副县长,我也没有太多的惊诧。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他往贺沛藉冬奥会冠军韩晓鹏家人的报道,所送的那副楹联是他自撰自书的。摄像机镜头前的潇洒恣肆,毫无“官”的矜持做作,这不还是那个胡成彪吗?前天,成彪把他的《沧桑随笔》送给我。展读玩味,一夜未眠。我突然把成彪甩出去的那一半和他自己留下的这一半合二而一:“官”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悲的是,时势人为地把“官”切割成“官性”、“人性”两个种属特质,并用“官性”把“人性”包裹得严严实实,又装裱得庄严伟岸,于是在与百姓之间便形成了仅使用“口腔”与“耳朵”(丁可语)两个不同器官功能的群体,继而也就阻断了彼此间心灵与情感的沟通与交融。当这种形态成为一种世态,所谓的“和谐社会”也就大打折扣了。诚然,把全部责任推给“官”们也有失公允,“官打民不羞”,“民”们的这种心态扭曲,溯源追根又该怨谁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圣人之言成为世俗之规,社会既然认可了这套程式,就有它存世的价值。假如不是把“优者”而是把“庸者”、“劣者”放到可以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官位”上,社会将会暗无天日,百姓也将苦不堪言。假如没有“黄金屋”、“颜如玉”这些“利禄”的诱惑,有谁愿意“青灯黄卷”、“寒窗十年”地去追求“功名”呢?“太守有酒能喝醉,书生无钱空慨然。”周沛生先生的诗句倒也直白、通达。“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敢于拂袖而去,是因为他尚有可以“采菊东篱下”的几亩薄地,无衣食之忧,才能有“悠然见南山”的轻松自在。
士子与仕途的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甘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自觉,且千古一脉,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回望历史,“做官”与“作文”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典范非苏轼莫属。他一生仕途坎坷,逆境之中仍留下了徐州治水、苏州筑堤、儋州兴学的煌煌政绩,当然,更有“文章千古事”的煌煌巨制。这些成就,绝非“有酒能喝醉”的“太守”们所能企及的。儋州有一处东坡祠,祠内藏有唐寅作画并题诗的碑刻。我将其中的诗抄录于此:“东坡在儋耳,自喜无人识。往来野人家,谈笑便终日。一日忽遇雨,戴笠仍着屐。逶迤还到家,妻儿笑满室。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诗明白晓畅,无须多解。用这样的境界打量成彪未必确当,但又何尝不可?抹去“口腔”与“耳朵”的隔膜,那便是诗人与诗人心路间的畅达。
说了半天,还是没谈到诗。成彪的诗我能读得懂,每一首都让我砰然心动。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小船无舵随风走,带起红莲一径香”这两句。丁芒先生说这首《微山湖夏日》是成彪的代表作,十分确切,这也正是成彪心路历程的自我表露。但仔细想,“随风走”的“小船”真的“无舵”吗?恐非尽然。船上无舵,舵在心中。忽觉我的这种理解颇近荒唐,这是在读诗,怎容得掺和进去逻辑推演?(戊子年霜月胡诌于是味书屋)
作者系高级记者、《徐州日报》原通联部主任
- 【关闭本页】 【返回顶部】 【打印此页】 【收藏此页】